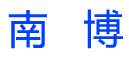《史记》体系地总结了我国古代前期文明的打开,不只是中华民族的名贵文明遗产,
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经典巨作。《史记》被鲁迅先生称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”。郭沫若先生也将其与至圣先师孔子相提并论,直接赞之为“功业追尼纲铮《史记》作为史学经典与文学经典,接连被翻译成各种外文,传抵达世界各地。《史记》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传达与影响途径,为新年代讲好我国故事供给了有利学习。
《史记》英译进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期间。第一期间首要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,体现为对《史记》的小规划零星译介。
这一时期,英国专家艾伦(Herbert J. Allen)在《皇家亚洲学会杂志》宣告了《五帝本纪》卷一的译文;英国专家理雅各(James Legge)翻译了《史记》中老子与庄子列传的内容;德范克(John De Francis)在《哈佛亚洲研讨》期刊上宣告《史记·淮阴侯列传》的译文;而美国专家卜德(Derk Bodde)的译著《古代我国的政治家、爱国者及将军:〈史记〉中三篇秦代人物列传》最具影响力,变成后续《史记》译者的重要参阅材料。此期间的译介内容非常有限,不成体系,却为西方读者掀开了陈旧中华文明的奇妙面纱,起到了启蒙、介绍与扶引的作用,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翻开的大规划《史记》翻译摆开前奏。
第二期间是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。这个期间《史记》翻译的篇幅和规划大幅添加,《史记》的零星翻译也显着增多,如美国汉学家鲁道夫(Richard C.Rudolph)在《远东学报》上宣告《史记·伍子胥传》的译文。其间还发生了4个节译著,别离为杨宪益配偶的《〈史记〉选》、美国汉学翻译家华兹生(Burton Watson)的《史记》、美国专家科尔曼(Frank Algerton Kierman Jr.)的《从四种战国后期的列传看司马迁的撰史情绪》、英国专家杜为廉(William Dolby)和司考特(John Scott)的《司马迁笔下的军阀及其别人物》,其间以华兹生的翻译最负盛名。
“我测验重视作品的文学招引力,把注释降到最低,极力译出更多的内容。”华兹生
的英译作品文学性与可读性强,极具招引力。他起先摘译了《史记》中文学性强的65篇,打乱了《史记》原作的次序,以汉朝作为源起,对全书从头编列后,选用归化办法进行翻译。到1993年,华兹生已译出《史记》130卷中的80卷,广受好评。
第三期间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,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倪豪士(William H. Nienhauser)组成由中外专家、海外我国人与海外汉学家构成的翻译团队,旨在“译出一种忠诚的、注解详尽的,并尽可以具有文学可读性与文体共同性的《史记》全译著”。倪豪士的译著保存了《史记》正本容颜,力求无缺再现《史记》的史学价值和文学个性,注重前史作业的精确性,除了附有古今中外衡量衡对照表、缩写表之外,每页都有详尽的歧义考证与有关常识注释,每章均附上了译者的评注,每卷还供给了全书的参阅文献目录以及有关作品。倪豪士选用异化翻译法,尽可以保存原作言语与文明特质,可谓西方最富学术价值的《史记》英译著。
“在对译作的传达中,译者、媒体、读者、生意人、赞助人、汉学家、谈论家之间要构成一种合力作用。”《史记》的译者皆为西方学术界极具影响力的汉学家,其英译著均有谈论,尤以华兹生和倪豪士的译著为最多。出名出书社发行的译著,一般在其封面或封底刊印推介言语,给予必定的介绍与宣传。与此一起,许多西方专家的作品中,凡触及我国前史和文学的选集与作品,常会引证或选用《史记》英译著,并在参阅文献中列出。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(John K. Fairbank)的专著《我国的思维和体系》(1957)和美国汉学家孙念礼(Nancy Lee Swann)的专著《食货志:公元25年前我国最早经济史》(1950),美国汉学家狄百瑞(William Theodore de Bary)、美籍我国人专家陈荣捷和华兹生合编的《我国经典选集》,以及美国汉学家白芝(Cyril Birch)编著的《我国文学选集》都录入了《史记》的英译著。这些年,越来越多的汉学家从叙事与列传视点对《史记》的文学性进行了深化研讨
和谈论,代表专家有美国汉学家约瑟夫·艾伦(Joseph R. Allen)、美国专家侯格睿(Grant Hardy)和杜润德(Stephen W. Durrant)等。《史记》的译者一般也是《史记》以及我国文明的研讨者,对《史记》英译的传达发扬了一起的作用。
《史记》在英语世界的传达与英语读者的等待相伴而行,跟着英语读者视界的不断拓宽,《史记》的译介呈现出期间性和接连性特征,译作也从零星逐步走向全体化。《史记》前期的翻译首要显示故事性和文学性,异质文明激起读者的逐异心思。读者由开始
对我国传统文明的探奇,走向晓得并企图全部深化地研讨。要使读者抵达“必定程度的视域交融”,就有必要处置因为无量文明差异所构成的开裂,因而华兹生会重组译作规划,改写原作,让译文轻松易读,投合西方读者的审美快乐喜爱。读者经过引人入胜的故作业节和生动叙事,添加了对中华文明和我国文明的晓得,构成了根据《史记》对我国典籍的认知,股动了《史记》的大规模阅览。
跟着倪豪士《史记》全译著的面世和更多译著的发生,英语读者有了更为多元的比照承受。从OCLC数据库检索来看,杨宪益译著(1979)的世界保藏量是239本,华兹生译著(1961)的世界保藏量多达823本,倪豪士译著(1994)的世界保藏量多至412本。倪译《史记》电子本钱的世界保藏量多达1163本,华译《史记》(1971)电子本钱的世界保藏量是252本。比较照而言,杨宪益译著在谈论、作品、选集里呈现的机缘较少,承受度比照低,短少广度与深度。华兹生译著受许多,承受面最广,对英语群众读者、译者、专家都有很大影响。其译著生动、传神,读来心旷神怡,可谓西方《史记》的经典译著。倪豪士译著信息丰富,内容精确,表达稳重正式,为学术界读者供给重要参阅,对这今后续的深化研讨发扬了不可以估量的作用。全体而言,华译首要拓宽了读者的“广度”,而倪译首要拓深了读者的“深度”,满足了专家集体的学术性需要。《史记》作为我国的文明经典巨作,现已跨越了国界,进入了世界视界。而《史记》在英语世界不一样期间的译介和研讨不只给西方“展示了一种了解世界的办法”,也让世界愈加晓得《史记》,晓得我国。
作者:徐琳 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
来历:我国社会科学网回来搜狐,查看更多
责任修改: